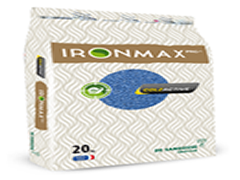近年来,全球农业界对″生物除草剂″寄予厚望。理论上,随着抗除草剂杂草的蔓延与化学农药监管趋严,生物除草剂似乎正迎来黄金机遇。最新报告显示,全球生物除草剂市场到2024 年估计约US$33.7 亿,预计到 2030年可达约 US$78.7 亿,年复合增长率(CAGR)约15.2%。然而,现实却显得冷静与生物农药、生物肥料的快速增长相比,生物除草剂仍在缓慢起步。为什么?
从″化学时代″走向″生物时代″,机遇看似无限
在过去半个世纪里,化学除草剂如草甘膦、莠去津等成为现代农业的基石。它们高效、廉价、易用——每英亩成本甚至不足10美元。然而,这种依赖也带来了隐忧:
杂草抗药性问题日益严峻。据估计,全球已有超过500种杂草对至少一种除草剂产生抗性;
化学残留、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引发的监管收紧趋势正在加剧;
欧盟、北美、澳大利亚等地陆续出台″减化″计划,鼓励低残留或生物替代品。
理论上,这正是生物除草剂的″完美风口″。它们源自微生物或植物提取物,对环境更友好,对非目标生物的风险更低,符合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方向。
现实:研发难、成本高、落地慢
根据农业生物制品领域的开拓者Pam Marrone博士的说法,生物除草剂的关键在于如何研发出能够与低成本除草剂竞争的产品。这句话道出了行业的核心矛盾:理想很美好,成本很骨感。
生物除草剂研发难度极高。首先,它必须在各种气候、土壤、作物条件下稳定发挥作用;其次,必须在农民能接受的价格区间内生产和使用。
Moa Technology的首席执行官Virginia Corless博士指出:″真正的难题不在实验室,而在田间找到一种能在实际农田中真正有效的生物除草剂。″
这意味着,生物除草剂既要满足科学标准,又要符合商业逻辑,而后者往往更难。
创新的路径:从″替代″到″增效″
在众多研发方向中,一种新的思路正在兴起——生物增效剂。
这类成分本身并不杀草,却能与除草剂协同,提高效率、减少用量。Moa Technology与农业巨头Gowan的合作,正是这种思路的代表。
这类″中间路线″策略或许更务实,与其一刀切替代,不如用生物科技提升化学除草剂的可持续性。
在非洲,化学除草剂昂贵且难以获得。肯尼亚的″牙签计划″(The Toothpick Project)利用尖孢镰刀菌(Fusarium oxysporum),开发出可防治杂草独脚金(Striga)的生物除草剂。
这种技术简单、低成本:农民只需将带菌牙签混入米饭中,制成种子包衣剂即可。如今,它已获得政府批准,并计划扩展至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。
这是一个有力的提醒:生物除草剂未必只能在高科技实验室诞生,它也可以源自田间智慧。
新工具加持,未来仍可期
如今,人工智能和基因组挖掘技术正在重塑这一领域。机器学习、AI、生物信息学等新工具能显著节省时间和资源。
从筛选微生物代谢物到设计新型分子结构,AI 正在加速″发现–验证–优化″的全流程。这或许会成为生物除草剂的下一个突破口。
生物除草剂的道路注定漫长。与生物农药相比,它既不″性感″,也不容易快速见效。但随着全球农业向低碳、减化、可持续方向转型,这条″慢热赛道″终将升温。
未来十年,我们或许会看到这样的局面:传统化学除草剂仍占主导,但与生物制剂的协同将成为主流;监管政策与资本资金,将推动更多研发进入应用阶段;从实验室走向田间,生物除草剂将真正成为绿色农业的重要拼图。
或许,这不是一场″革命″,而是一场″进化″。
来源: 公众号:城食有农